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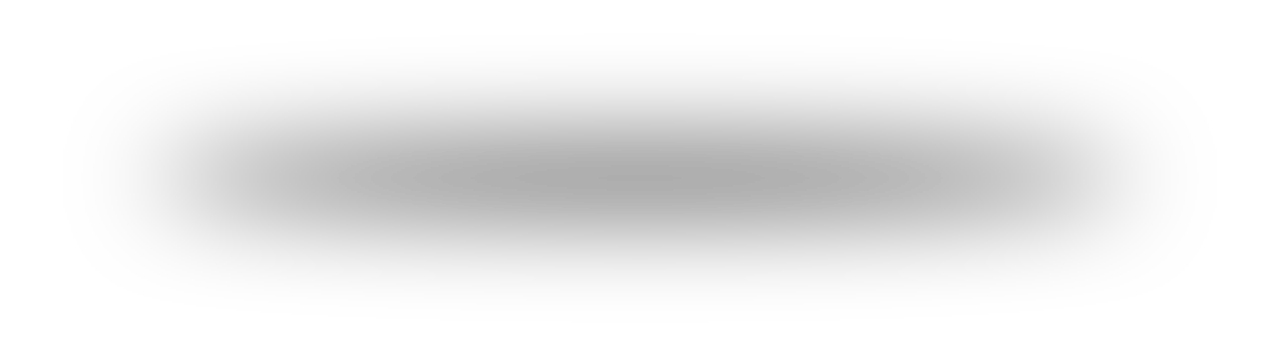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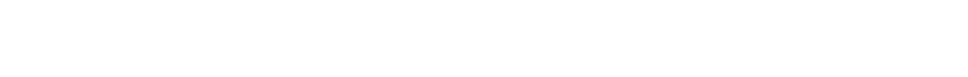
破产管理人行使合同解除权情形下共益债的认定
文/郑建国 郑杰
一、 个案:房地产合作开发项目中资金提供方的债权性质如何认定?
S公司是一家房地产项目开发企业,于2010年与五位合伙人签订了共同开发重庆两项目的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由五合伙人提供资金,以S公司的名义购买土地并进行具体开发工作,各方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一年后又签订了相关补充协议。2015年,S公司与五合伙人之间就两工程项目的权属问题发生纠纷,五合伙人向仲裁委申请仲裁,最终双方达成了按份共有两项目的调解协议并由仲裁委确认,但未至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2016年,S公司因经营不善破产,两项目开发工作因此停滞,有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对S公司进行破产重整并获受理。而后管理人没有再继续履行与五合伙人的合作开发协议,项目开发工作完全停滞下来。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应视为管理人已经解除了合作开发合同。后五合伙人与S公司就两案涉项目的归属问题纠纷不断。五合伙人于2018年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在案涉两工程项目中享有基于共有关系的取回权,而管理人认为五合伙人的资产权益不仅不属于物权,还只能认定为债权中的劣后债。各级法院均认为五合伙人对案涉两项目享有的应当是债权而非物权,但对于债权的性质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五合伙人要求将其资产权益认定为共益债,遭到管理人和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强烈反对,五合伙人遂就此提起诉讼。
S公司是一家房地产项目开发企业,于2010年与五位合伙人签订了共同开发重庆两项目的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由五合伙人提供资金,以S公司的名义购买土地并进行具体开发工作,各方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一年后又签订了相关补充协议。2015年,S公司与五合伙人之间就两工程项目的权属问题发生纠纷,五合伙人向仲裁委申请仲裁,最终双方达成了按份共有两项目的调解协议并由仲裁委确认,但未至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2016年,S公司因经营不善破产,两项目开发工作因此停滞,有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对S公司进行破产重整并获受理。而后管理人没有再继续履行与五合伙人的合作开发协议,项目开发工作完全停滞下来。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应视为管理人已经解除了合作开发合同。后五合伙人与S公司就两案涉项目的归属问题纠纷不断。五合伙人于2018年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在案涉两工程项目中享有基于共有关系的取回权,而管理人认为五合伙人的资产权益不仅不属于物权,还只能认定为债权中的劣后债。各级法院均认为五合伙人对案涉两项目享有的应当是债权而非物权,但对于债权的性质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五合伙人要求将其资产权益认定为共益债,遭到管理人和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强烈反对,五合伙人遂就此提起诉讼。
三 、不宜将管理人解除合同后相对方的权益认定为共益债
由于共益债的存在实际上是公平清偿的一个例外,会对全体债权人的清偿利益产生重大影响,故必须从严认定。我们认为,将管理人解除合同后相对方的已给付部分认定为共益债,至少有三点不妥之处:
1.人为制造了不承担破产风险的超级债权人,严重损害公平清偿
《企业破产法》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对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也只有这样,各债权人才有可能心平气和地接受按比例清偿而非全额清偿的方案。而管理人解除合同情形下的联合投资开发合同的相对方实际上和破产企业的其他债权人并无本质区别。更何况在全体债权人中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已经将合同义务全部履行的,如果按该观点的逻辑,未将合同义务履行完毕的债权人可因管理人行使合同解除权而优先受偿,已经履行完毕其义务的债权人反而只能认定为普通债权,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对其他债权人来说也是极不公平的。
2.从体系上看,与《企业破产法》的其他条文存在严重冲突
首先,从《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内部看,第(一)项明确规定了应将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认定为共益债,但并未规定将“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认定为共益债,且该条的其他几项所述情形中,引起基础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都发生于破产程序启动之后,不当得利岂有例外之理?其次,从第四十二条与第十八条的关系看,如果将管理人解除合同后对方的权益人全部认定为共益债,就大大减损了管理人合同解除权的效力,架空了破产合同解除制度,使其成为了部分债权人规避破产风险、优先抽身的工具,显然不妥。最后,该法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管理人或者债务人依照本法规定解除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其意涵非常明确,即管理人行使合同解除权后,若因此给债权人造成了损失,该部分损失可以申报债权,其余部分只能依法定程序和一般标准予以认定。从该条亦可以看出立法者并无将合同相对方权益认定为共益债的倾向。
3.时间要件和共益性存疑,与共益债的立法本意不符
我们认为,在管理人行使合同解除权所导致的不当得利情形中,判断债权债务关系发生时间应当以其基础法律关系,即合同关系为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协调《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与其他几项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逻辑自洽,才能实现共益债的立法本意。如文首案例中,应当认定其债权债务关系的成立时间是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的2010年,而非管理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2016年。其次,共益债顾名思义,必须是清偿之对全体债权人有益才能构成。将管理人解除合同后对方当事人的权益认定为共益债,会大大减少其他债权人的受偿金额,于全体债权人而言没有任何共益之处,且此类债权人并没有值得法律特别保护的理由,不能给予差别对待。故这些债权在时间要件和共益性上都有明显欠缺,不符合共益债的成立要件。
四 、正确把握共益债认定标准,回归立法本意
1.正确处理民法与破产法之间的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些以《民法典》或原《合同法》中关于合同解除法律后果的规定为依据,将管理人解除合同后对方权益认定为共益债的情形。如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认为若无法恢复原状,就应当将对方权益认定为共益债。我们认为,这是没有正确处理民法与破产法关系的体现。试想,《民法典》还要求当事人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但在破产情境下怎可能实现呢?实际上,民法与破产法间应是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民法上的内容显然只是对一般情境下解除民事合同后法律后果的规定,并不能当然推及到破产领域。共益债作为破产法上的特殊制度安排,其认定只能以《企业破产法》为唯一依据。
2.应同时对共益债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进行审查
在司法实践中,不仅要注重对形式要件,即时间要件和原因要件的审查,也要注重对实质要件的审查。满足实质要件的条件有二:一是债权人之债权须有值得特别保护之理由。如文首案例中,不能以五合伙人的债权比重作为衡量标准,而应判断其债权与其他债权人相比有无本质差异。在该案中,五合伙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形成时间是早于破产程序启动的,其所投入资金也早已转化为项目资产,这与其他债权人的债权相比并无本质差异,反观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不当得利情形,一般都是他人在破产程序启动后向债务人误转账,或管理人在破产程序启动后错误处置了他人财产等,这类债权真正形成于破产程序启动之后,且无法通过正常的债权申报程序受到保护,因此具备值得特别保护之理由;二是清偿债权人的债务会使全体债权人客观上受益。在本案中,清偿该债既不能防止债务人财产虚增(因为案涉两项目本身就登记在债务人名下),也无益于增加债务人财产(区别于破产程序启动后新注入的合作资产)。故从实质要件来看,该案中五合伙人的债权也完全不具备认定为共益债的条件。
3.正确处理破产法第十八条、四十二条及五十三条之间的关系
应当明确,共益债认定的主要依据必然是《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该条未明文列出的情形绝不能任意认定为共益债。立法者既然将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合同后新产生的债务,而非管理人解除合同后对方当事人的权益写入四十二条,就证明其已经作出了选择,即后者不能认定为共益债。如果将此类债权债务以“不当得利”为由生搬硬套地认定为共益债,甚至不惜到民法上去寻找依据的话,显然就将该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管理人合同解除权制度架空了,这显然是不当的。《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三条已经为管理人解除合同的对方权益保护作出了制度安排,即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这并不意味着债权人的其余部分债权就不能得到保护,其仍可以依照《企业破产法》中相关规定申报债权,但因无法律依据而不能认定为共益债。
五 、结 语
共益债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全体债权人的清偿利益,也极大地影响整个重整进程的成功与否。故对其认定必须坚持依法、从严的原则,在正确把握《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时间要件的同时,也要重视对共益要件等实质要件的审查,切不可过度扩大共益债的认定范围,否则将极大地破坏全体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将破产企业拖入重整失败的险境。
最新动态
- 执行实务|执行和解协议已签,对方反悔拒不履行?律师教你这样维护权益! 2025-04-15 23:22:12
- 知我见 | 从典型案例浅谈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如何适用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系列一】 2025-04-01 00:00:00
- 新声丨付海平:坤源衡泰数智化建设的路径 2024-06-11 00:00:00
- 新声丨付海平:区域规模律所的“四有”之度 2024-02-17 00:00:00
- 献礼整合十周年 | 李毅维:强优势、补短板 助力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区域律所发展论道 2023-12-06 00:00:00
- 献礼整合十周年征文 | 付海平:区域律所由大到强的精益之路 2023-11-20 00:00:00
- 视点 | 雷宇、苑春壹:安全保障义务人侵权责任的承担——以“一杯水泼出11万”事件为例 2023-04-25 00:00:00
- 视点 | 彭兴洪:收到违约金要不要缴纳增值税呢? 2023-03-22 00:00:00
- 视点 | 陈涛:驾驶证扣满12分后你还敢开车吗? 2023-03-20 00:00:00
- 视点 | 刘小华、雷泽权、马巧巧:以2022发布案例视角,析医疗机构纠纷风险防范之一——麻醉篇 2023-03-10 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