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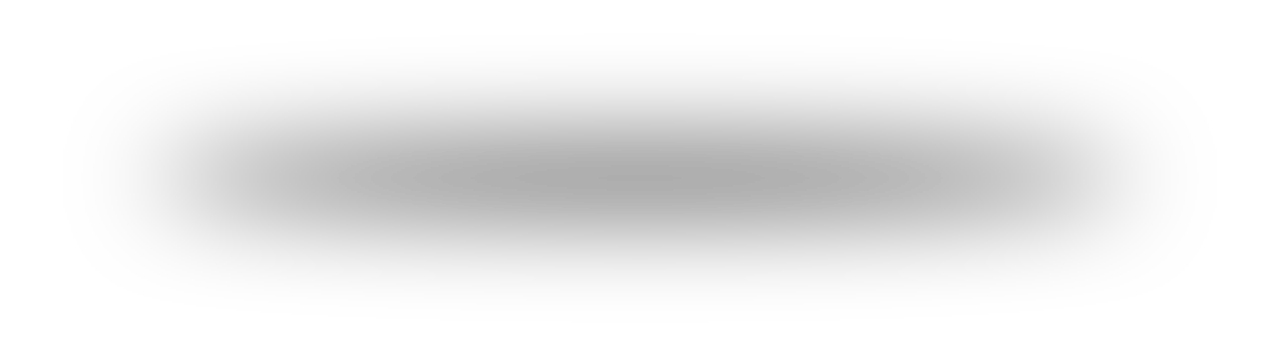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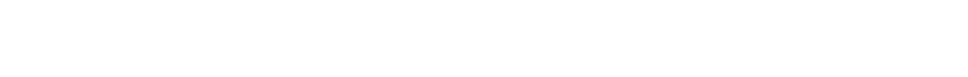
产权划分裁判书与破产取回权的关联性探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若债务人没有基础权利而占有了他人财产,标的物存在且能够区别于债务人破产财产的,则该标的物的权利人可以向管理人申请取回。破产实务中,如何确认申请人符合取回权的主体资格,是正确适用本条的关键点之一。
申请人实现取回权,首先有义务证明自己对标的物享有取回的基础权利。申请人除向管理人提交申请书外,还需举示证明自己系权利人等相关证据,即申请人有必要提供关于标的物的权利证书。一般情况下,动产的权利凭证仅需提供购买凭证即可,不动产需提交产权证书。某些特殊情况下,申请人并无这些标的物的购买凭证或产权证书,若他们持有法院或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判,可否依据这些生效裁判认定申请人系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人或用益物权人呢?
民事诉讼案件,按诉的种类可分为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形成(变更)之诉,与之相对应,经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审理后作出的判决、裁定、调解文书可分为给付性裁判、确认性裁判和形成性裁判(又称变更性裁判)。确认性裁判和形成性裁判均是关于财产归属的裁判。在破产环节,这两类裁判的法律效力明显不同,其中形成性裁判依法可以作为申请人拥有取回权的权利凭证,而确认性裁判却没有等同于产权证书的权利凭证属性。
一、确认性裁判与形成性裁判的概念及区别
确认性裁判,指审理确认之诉案件中对确认某种法律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的事实状态进行确认而作出的裁决或者判决。形成性裁判是指在法院或仲裁机构审理变更之诉案件中,以改变或者消灭现存的某种法律关系为目的而作出的裁决或判决。确认性裁判与形成性裁判均系对涉案财产的产权进行划分而形成,但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
确认性裁判常存在于确认之诉中,也可能存在于给付之诉中,确认性裁判,包括确认性判决书、确认性仲裁裁决书、确认性裁定书(如执行裁定),亦包括确认性调解书。其裁判主文表现为确认权利人对现存财产的所有及用益等法律状态,系对当事人之前协议中对财产归属状态持续存在的司法确认。
形成性裁判通常存在于形成之诉(变更之诉)中,但也可能存在于确认之诉或者给付之诉过程中。形成性裁判,包括形成性判决书、形成性仲裁裁决书、形成性裁定书(如执行裁定),亦包括形成性调解书。其通过改变现存法律关系以实现新法律状态,具有明显的改变原有物权关系内容。
二、经典案例指引①
2013年,某甲房屋开发公司因资金及资源不足且已有一定量的到期债务尚未清偿,乙公司的状况比甲略好,自然人丙有一定资金实力且想通过房地产开发掘金,一次偶然的茶会让三方达成了合作开发某楼盘的协议。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出资以甲公司的名义拿地开发,乙和丙参与建设管理,项目的收益按甲3乙3丙4的比例分享。并约定各自与本项目无关的债务由各自独立清偿不能与本项目关联。
在合作投资生效后,三方均各自依约投入了上亿的资金及人力管理,在项目开发进度达60%左右时,甲公司终因债务危机影响了项目的正常进度,乙和丙看到了项目在甲名下的风险,遂于2015年依据合作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向xx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仲裁委依据三方协议确认乙、丙各自享有约定份额的土地开发权及项目收益权。
2016年,三方在仲裁委主持下达成了仲裁调解书,该调解书确认甲、乙、丙各自依协议约定比例享有开发项目中土地使用权的使用权以及项目收益的分配权。且在申请人及被申请人的共同要求下,仲裁委依据仲裁调解书制作了仲裁裁决书②,该裁决书的主文又一次确认了三方在仲裁调解书中的关于投资及权益占有与分配的内容。
在仲裁委作出裁决的半年后,甲公司终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在债权申报阶段,乙、丙两方依据该仲裁裁决书向管理人提出了取回权申请,要求管理人执行仲裁裁决书,将他们占有的70%的开发土地及收益权取回。
管理人认为乙、丙的情形,其持有的裁决不是证明他们对取回物享有使用权的权利证书,故不符合我国破产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对涉案的争议财产不享有取回权。
在管理人向乙、丙二人送达债权不予确认的意见书后,二人作为共同原告向受理重整案件的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取回权之诉,要求法院认定管理人拒不执行仲裁裁决书的行为违法,并请求依法确认他们对项目中属于他们份额的土地及已开发房屋的收益享有取回权。本案经过一审、二审及再审复查,各级法院均未支持乙、丙二人的诉讼请求。三级人民法院不支持合作投资人诉讼请求的理由分别如下。
1. 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理由
一审判决理由归纳为:
其一,取回权是民法上物的返还请求权在破产程序中的一种表现形式,破产财产取回权属于物上请求权,权利人行使取回权的财产首先应当属于权利人所有;取回权得以实现的前提为相应财产仍独立存在,被债务人占有且不属于债务人。
其二,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涉案项目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在某甲名下,某甲系涉案项目土地使用权的不动产权属证书所记载的权利人,虽然XX仲裁委员会作出的XX号裁决书确认二原告对案涉土地使用权按份共有,但因未办理变更登记,在破产程序中亦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不能对抗某甲的其他债权人。
其三,由于二原告与某甲签订的协议性质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故二原告实际上将其与某甲按份共有的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共同投资涉案项目,土地使用权已经转化为项目投资,而该项目的开发商系某甲公司,二原告不是该项目的开发人,其仅能享有项目中各自股份比例的投资收益分配权,而不具有案涉房地产开发项目及所占土地的物权, 也就不享有该物的取回权。
2.二审判决维持的理由
二审判决理由归纳为:
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权利人在破产程序中行使取回权的标的物,应是被债务人占有而由权利人享有所有权或用益物权的财产。
其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的规定,导致物权变动的生效法律文书首要必备条件是要具有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内容, 即变动或者消灭当事人之间原来存在的物权归属关系。本案中,在仲裁裁决作出前,各合作开发人之间达成《调解协议》,确认各方之间签订的相关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且项目土地使用权和开发权属于二上诉人与某甲公司共有,其内容仍是维持各合作开发人之间现有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关系,以及对各方基于合作开发关系所共同享有的权益与相应义务予以确认。而仲裁委XX号仲裁裁决是在当事人达成前述《调解书》并请求仲裁裁决予以确认的基础上作出,其公权力介入主要体现在对《调解书》内容的合法性予以确认并赋予其可执行内容的强制执行效力,该仲裁裁决所裁决事项本质上是依据当事人合意对合作开发人之间基于共同出资所形成 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确认,并非改变合作开发人之间既存的权利义务关系,因而不属于能够直接导致物权变动的形成性裁决,而属于确认性裁决。
其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在仲裁裁决所确认的合作开发人对土地使用权的共有权益未依法办理登记前,二上诉人并不享有物权性质的权益。其四,各方当事人约定共有的项目开发权,应是各方参与开发活动、分享开发利益的权利,在项目土地使用权不能进行直接分割取回的情况下,该权利亦不能成为破产取回权的标的。
3.最高院再审复查裁定驳回的理由
最高院判决理由归纳为:
其一,尽管仲裁委第XX号仲裁裁决确认案涉项目土地使用权由二申请人和某甲公司共同出资购买,土地使用权及开发权为上述三方共有,但仲裁裁决书也同时确认了继续履行当事人之间的合资合作开发协议及合作经营模式,即继续由某甲公司持有土地使用权,以某甲公司名义进行房地产开发。故原审判决认为仲裁委XX号裁决事项本质上是依据当事人合意对合作开发人之间基于共同出资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确认, 并非改变合作开发人之间既存的权利义务关系,因而不属于能够直接导致物权变动的形成性裁决,而属于确认性裁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其二,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案涉土地使用权已设定抵押,抵押担保的债务及项目其他债务尚未清偿,案涉土地上已进行了一期、二期开发,土地使用权已融入到项目房产中,且部分房产已对外销售。二审法院基于本案房地产开发实际情况及某甲公司进入破产重整后保有案涉项目资产进行后续开发经营以提升债务人整体财产价值的实际需要,未支持二申请人基于物权请求权原理行使取回权并无不当。
三、关于财产划分裁判与取回权的关联探析
1. 行使取回权的主体资格
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行使取回权的人只能是所涉财产的权利人。申请人要将涉案财产取回,首先就必须证明自己是该财产的权利人,此权利包含所有权或用益物权。如果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自己是财产的权利人,管理人可以申请人不是法定权利人为由否定其取回请求。
权利人持有的凭证,必须是有效的权利凭证,而非作废的或者不足以证明权属关系的其他文书。
2.关于权利凭证
基于所涉财产的种类及性质不同,证明自己系财产权利人的证据也不同。如一般动产,只要有购买的凭据或取得的来源性文件即可;若是不动产,则应当提供有效的所有权证书或其他权利证书,证明自己是财产的合法权利人。
依据我国《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一般情况下需经依法登记才发生效力;未经登记则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此条规定的除外,是指没有到物权登记部门登记也可以发生法律效力的特殊情况。不动产的权利凭证,一般情况下是指由物权登记部门下发的所有权证书,特殊情况下还包括该条中的法律另有规定的其他凭据。
3.辨析确认性裁判与形成性裁判
具体哪些属于我国《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中的法律另有规定情形呢?这些情形可以不经登记而发生法律效力,它们的法律依据和具体种类是什么呢,我们简要阐述如下。
依据我国《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消灭的法律文书或征收决定等裁决即形成性裁决,是《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规定的例外情形之一。本条所规定的政府或司法机构作出的形成性裁决,即是可以不经登记可发生法律效力的例外情形。该条明确规定只有形成性裁决是例外情形,排除了确认性裁决作为证明产权权属凭据的可能性。从诉讼法理论上看,确认判决和给付判决的效力均仅及于诉讼当事人之间,而不能约束案外第三人。故即使裁判书中确认了产权归属,如未到主管部门处办理变更登记或更正登记手续,仍因缺乏公示手段而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在破产程序中即不能对抗其他债权人;而形成判决的效力具有对世性,故形成性裁判可以直接作为权利凭证来使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第七条亦规定,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在分割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等案件中作出并依法生效的改变原有物权关系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变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九条所称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
据此可以看出,能够与取回权关联的形成性裁判有以下类型:
(1)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在分割共有财产案件中作出的改变原有物权关系的判决(裁决)书、裁定书、调解书;
(2)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变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
(3)人民政府作出的征收决定书。
综上,我国民法典规定的不经登记亦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形,须以另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为前提。确认性裁判没有我国现行法律依据来支撑,故不能成为未经登记而发生法律效力的权利凭证。形成性裁判,有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等法律基础的支撑,系不经登记即可发生法律效力的权利凭证,其效力类同于物权登记机关的权利证书。在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当债务人没有权力基础占有该财产、该物与债务人的财产可区分且客观存在时,申请人可将其持有的形成性裁判作为主张取回权的有效凭据。
注释:
①案例系依据(2018)川09民初119号判决、其二审作出的(2019)川民终954号判决以及申请再审作出的(2020)最高法民申4763号民事裁定书所涉案件,适当精简归纳。
②裁决书文号:(2015)遂仲裁字第24号裁决书
最新动态
- 执行实务|执行和解协议已签,对方反悔拒不履行?律师教你这样维护权益! 2025-04-15 23:22:12
- 知我见 | 从典型案例浅谈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如何适用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系列一】 2025-04-01 00:00:00
- 新声丨付海平:坤源衡泰数智化建设的路径 2024-06-11 00:00:00
- 新声丨付海平:区域规模律所的“四有”之度 2024-02-17 00:00:00
- 献礼整合十周年 | 李毅维:强优势、补短板 助力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区域律所发展论道 2023-12-06 00:00:00
- 献礼整合十周年征文 | 付海平:区域律所由大到强的精益之路 2023-11-20 00:00:00
- 视点 | 雷宇、苑春壹:安全保障义务人侵权责任的承担——以“一杯水泼出11万”事件为例 2023-04-25 00:00:00
- 视点 | 彭兴洪:收到违约金要不要缴纳增值税呢? 2023-03-22 00:00:00
- 视点 | 陈涛:驾驶证扣满12分后你还敢开车吗? 2023-03-20 00:00:00
- 视点 | 刘小华、雷泽权、马巧巧:以2022发布案例视角,析医疗机构纠纷风险防范之一——麻醉篇 2023-03-10 00:00:00
下一篇
“售后返租”的合规红线及防范
